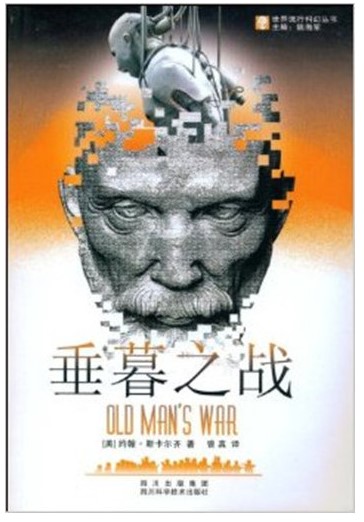阅读笔记:《垂暮之战》
## 阅读笔记:《垂暮之战》
作者:约翰·斯卡尔齐
阅读时间:2015年11月8日,2015年11月23日,2015年11月24日
说实话,连续半个月平均每天打八千字的活动量所带来的疲劳,使得我经常会翻得很不上心。
四个字,如此乏力却又如此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人生。几个字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关于她每日的所见所闻或她的工作状况,关于她的兴趣所在或心仪的旅行去处。你永远无法得知她最爱的颜色,或她喜欢如何打理发型,或她投谁人的票,或她的幽默感水准如何。
“我将把每个段落念给你听,”她说。“段落结束的时候,如果你明白并且认可听到的内容,那么请在段落下签上你的名字和日期。如果你有问题,请在段落结束的时候问我。如果你不明白或者不接受我念的或解释的内容,那么请不要签字。你懂了吗?”
我曾经对祖父说,等我到了他的年纪,科学家们一定能找到大幅度延长人类寿命的方法。他报之以大笑,告诉我,他也曾经如此认定,可到头来他还是变成了一个老头儿。
人们的寿命能够延长,也的确得到了延长,但多出来的年份还是作为老人而活。关于这点,改变的东西不多。
看看你自己:当你在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甚至五十五岁的时候,还尽可以觉得能够对抗整个世界。
你到了七十五,朋友们都已逝去,你也至少换了一个主要脏器;你一个晚上要起四次夜,上一段楼梯或台阶总要让你气喘吁吁,还总有人对你说在这个年纪你算是体形不错了。
期冀变得年轻是一回事,但永远离弃你所熟识的一切、你认识的和挚爱的每个人、在七十五年的跨度间体验过的每件事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和你的整个人生说再见,这他妈的还真是件事情。
“我才不在乎上年纪呢。”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在乎,”我说。“可是衰老还是找上了我。”
在我的想象中,这和几百年前有人坐上四轮马车驶向西部有些类似。人们哭泣,人们想念他们,然后回去各忙各的。
和他有过一番促膝长谈,我为一些事情道歉(真诚地),也同等真诚地告诉他我有多么为他所成为的这个男人自豪。之后,我们坐在门廊上,喝着啤酒,看着我的孙子亚当在前院里殴打一只儿童简易棒球,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好长时间。分开的时候,我们怀着爱意互道珍重,就和理想中的父子一般。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们希望观看我们离开卫星轨道的话,我们将把视频信号接到甲板上的观测室。观测室面积相当大,能容纳所有新兵,因此不需要担心座位问题。Henry Hudson的速度很快,因此到了明天早餐时地球将只有一个非常小的碟子大小。午餐时将只是天空中的一个亮点。这可能是你们最后看一眼家乡星球的机会。如果这对你们来说有深刻意义的话,我建议你们不要错过。
“瞧呐,”我说。“我们的人生,那是我们曾经呆过的唯一地方。我们认识的爱过的人都在那儿。现在我们正在离开。难道你们没有点儿感受吗?”
最基本的思维和情感反应进行大脑监测,每个人的大脑处理信息和经验的机理多少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方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就好比每个人都有五个手指头,却没有相同的指纹。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就是要鉴别你们的‘精神指纹’。
植入传感器的第二原因,他们记录下你们的大脑活动内容,实时地反映你们的思维活动。换个说法,它们在不断传送你们的所思所想。这很重要,因为不同类型的思维活动、意识并不能被记录。除非它们正在转换。
人老的时候,身体的什么部分都会老。只有一样可以继续使用下去,那就是你的思想,你的知觉,你的自我意识。
“谢谢,”我对曾经的自己说:“感谢你所有的一切。”
你的血液已被置换为强化血液,一个更为先进的系统,比原有血液提高四倍携氧能力,并可防止由疾病、化学毒素以及因失血而带来的死亡威胁。我们的猫眼视觉技术将大幅提高你的视觉能力。被强化的视网膜和视觉细胞所带来的更优越的视觉成像技术让你能适应任何自然环境,特别的视觉信号放大技术使你可以在低能见度的环境里获得清晰的图像。
关于超感觉系统。这套被增进的超感觉系统将使你在触觉、嗅觉、听觉和味觉上达到从未有过的敏感度,扩展的感知定位能力和优化的知觉链接将大幅提高你在各种感知类型上的感觉能力,你从第一天就会有全新的体验。
你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你们所保卫的宇宙能让你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以及所有人类的孩子成长和繁衍下去,想到这一点,尽管代价高昂,但意义重大。
叫醒你们的原因非常简单,你们不需要更多的睡眠了。感谢你们的新体格吧,现在你们只需要每天睡两小时!要睡八个小时不过是因为习惯。睡觉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两个小时足够你们用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只有两个小时觉可以睡。
这只是小意思,你相信你能做到什么,你就能做到什么。
它是这么说的:‘这是我的枪,这儿有很多类似的枪,但这一只才是我的枪。我的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它是我的生命,我要像对待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我的枪。我的枪,离开我就是废物。我,离开我的抢就是废物。我要正确地开火,我必须果断射击那些企图杀死我的敌人,我必须在他射中我之前射中他,而且我一定做到得这一点。’
“在体能训练上,你们已经学会怎么超越那些想象中的体能极限。”
现在到了要丰富你们的精神世界,去除你们的成见和习惯性思维方式的时候了。
每场战斗都是新的,全新的战斗环境,全新的个人体验。
作为一个士兵要牢记,你会经常和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种族战斗。你必须快速地思考,而且不要假设应该怎么怎么去打,否则你马上就挂了。
“我说,我认为CDF的问题在于,他们并非战斗力不强,而是武力被滥用。”
注: 你并非战斗力不强,而是没有被正确地利用。
我们大老远跑到某个星球,不仅是不知道我们要与什么作战,而且是连想象都没法想象。
“我爱看书,”Alan说,“在星期天早上看一本又大又厚的精装书。”
如果你能回去,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同样的生活?你已经那样活过一次了。
之所以为人,有一个因素是我对别人有意义,别人对我也有意义。
“OK。这个,是我们的宇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宇宙,是唯一一个因存在量子理论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宇宙。比如说,每当我们确定一个电子正在一个确切的位置上,我们的宇宙就可以被这个电子的位置所定义,但在其他宇宙,这个电子的位置则完全不同。懂不懂?”
“我们会进入多元宇宙,而每一个宇宙好像都没什么区别。但我以前在科幻小说上看到说,每个‘或然宇宙’都相当不一样。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宇宙。”
因为存在各种可能性的事件,所以宇宙在不停地被创造出来,我们一跃迁,我们准备跃迁去的那个宇宙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跃迁成功,因为那个宇宙和我们原来的宇宙靠得非常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可能的事件分叉也越多,你回去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了。甚至只要过一秒,你就几乎不可能回去了。回到一年前我们所在的宇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我们应该多往好的方面想,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疯狂的计划但是它可能很有效。你们越全力以赴,它就越会成功。明白吗?
“特种部队的士兵,他们没有任何私人事务,因此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交谈的。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几乎全靠脑伴交流,因为这样更快,而不是我们对用嗓子说话有什么偏见。我们出生就带着脑伴,脑伴是第一个和我们说话的‘人’,它简直就算我们其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几乎只用脑伴交流,不要对此太不爽。而且,我已经命令全队,如果他们要跟你交流什么,就要用开口说话的方式。”
“没必要,长官。”我说,“我也能用脑伴。”
“你跟不上的。”Crick少校说,“你的脑伴交流是一种速度,我们是另一种速度,是你的两倍。如果你急着要我们传送个什么,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看起来就象突然连接然后又突然断线一样。和你说话就像和小孩子一样要慢吞吞的。别介意我这么说。”
“我没多少有趣的事,”Jane说,“我只有六岁,几乎还没时间做任何事情。”
“我去年做的事情比我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要多。”我说,“六年足够长了。”
“多谢,长官。”这个士兵把他的盘子放到桌上,“我是Sam Mendel下士,这是二等兵George Linnaeus,Will Hegel,Jim Bohr,还有Jan Fermi(译注:前面提过,特种兵的姓多取自名人,这五位的姓分别来自:孟德尔,奥地利遗传学家;林奈,瑞典博物学家;黑格尔,德国哲学家;波尔,丹麦物理学家;费米,美国物理学家)。”
注: 聊看一些名人,有助于在作品中使用。也就是提到的这些人,有时候记忆让作品本身更加地丰富。
“我很想知道,长官,”斜靠着桌子的Bohr说,“你入伍之前可谓过了一辈子。那到底像什么?”
“像什么?”我说,“我现在的生活,还是之前过得的那些日子?”
“随便哪个。”Bohr说。
“我喜欢我的生活,”我说,“我不知道这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是很刺激或者很有趣,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过去那段生活到底如何,我当时没有思考过。我也从来没想过我即将面对新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情况下,还去做某些事情。”
“因为你还没老。一个普通的七十五岁的人,和你有质的不同。”
你们的生活像什么?”
Mendel看看他的战友,他们也在看着他。“这些东西我们平时没考虑过,长官。”Mendel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初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出生’的。在我们看来,你却很不一样。在你进入这个身体之前,你有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这看起来效率很低。”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加入特种部队,你会是什么?”
“我不能想象。”Bohr说,其他人也点点头。“我们都是士兵,我们要做士兵作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你这么好奇,”Mendel说,“因为你可以选择生活,你可以选择另一种活法。这太奇怪了。”
“你过去做什么?”Bohr问,“在另一个生活里。”
“我是这个作家。”我说,他们相互看看。“怎么了?”我问。
“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长官。”
“我只是希望我还有点时间调整我的这个习惯性思维。”
“现在形势变化得很快。”
“跟我谈谈她。”我在休息室刚学完使团协议,她就出现了。
“跟我谈谈她。”几个小时以后她又来了,在另一个地方。
“Kathy有一次差点和我离婚,”我说,“我们已经结婚十年了,我有了外遇,Kethy发现后狂怒不已。”
“她为什么会介意你和别人发生性关系?”Jane问,
“不是性的问题。”我说,“是我跟她撒了谎。性的问题在她看来只是个男人荷尔蒙方面的一个弱点,撒谎则是对她的不尊重,而且她不希望和一个不尊重她的男人过日子。”
“那为什么你们没离?”
“因为除了这个不愉快,我爱她,而且她也爱我。”我说,“我们没离婚是因为我们希望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她几年以后也出了同样的事。所以我猜你会说我们扯平了。打那以后我们相处得比以前更好。”
“跟我说说她。”后来Jane又来问。
“跟我谈谈。”Jane又出现了。
自从我加入Jane的排之后,特种兵就不再恭谦地和我用语言交谈了,而用他们的脑伴模式进行交流。如果我要和他们并肩作战,那我们就得按照他们的方式来。
特种兵之间传递信息简直比我眨眼睛还快,我还没看完第一条信息,他们的会谈已经结束了。最麻烦的是,特种部队不仅仅传递一个文本或者视觉信息,他们利用脑伴传递情绪信息的能力,瞬间传递出某个情感,就好像作家写文章的时候加标点符号。
本文出自 个人生活数据分享,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及相应链接。
本文永久链接: http://sikaoa.com/2015/11/24/3889